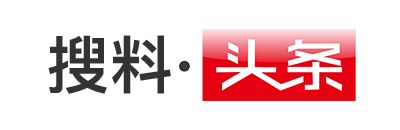聚焦“雙碳”,做好能源轉型大文章
已有人閱讀此文 - -實現(xiàn)“雙碳”目標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(zhàn)略決策,也是推動高質量發(fā)展的內在要求。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,要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。3月10日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國家電網公司一級顧問、國家能源集團電力領域首席科學家黃其勵,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(yè)工程學部副主任、國家能源集團科技委副主任顧大釗。兩位院士表示,今年兩會期間,黨中央和國務院很多新的提法,給能源轉型指出了很好的路徑。
談煤炭發(fā)展
做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
“煤炭一直是基礎能源,現(xiàn)在又提出叫‘兜底能源’,我認為在我們國家只有煤炭才能稱得上‘兜底能源’。”顧大釗說,煤炭資源要做到綠色開發(fā)、清潔利用、清潔轉化,才能為實現(xiàn)“雙碳”目標做支撐。
黃其勵表示,要把能源利用效率提上來,首先要把在同樣的GDP下的煤碳的消耗量減下來,即煤炭消耗總量和消費強度降下來,首先在煤炭做文章。第二是在生產方式上做文章,就是提高煤炭科學產能的水平,提高煤炭生產的“潔配度”,提高信息化數(shù)字化的水平。
說起煤炭清潔轉化,不得不提煤化工產業(yè)。黃其勵認為,在煤炭的功能上,煤炭既是能源也是資源,發(fā)展煤化工是煤炭清潔利用的一個很好的出路,也就是說延長加工鏈,不是“挖出煤來就上火車”,還是要繼續(xù)在煤化工多聯(lián)產上下功夫。
煤化工要高端化、多元化、低碳化發(fā)展,這里面還有水資源制約的大問題。據顧大釗介紹,我國每采1噸煤大概產生兩噸礦井水,目前我國每年有50億噸礦井水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。國家能源集團變害為寶,實現(xiàn)了礦井水與煤化工產業(yè)耦合發(fā)展,從2017年開始,年產100萬噸油品的鄂爾多斯煤化工項目就已經全部依靠礦井水來進行生產。
“煤制油也是‘兜底油品’。現(xiàn)在我們國家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70%,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40%,如果說一旦出現(xiàn)特殊情況,國內每年只能生產2億噸原油,怎么辦?” 談及煤基能源,顧大釗認為,發(fā)展煤制油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國家的油品安全。
談新能源發(fā)展
未來實現(xiàn)“雙碳”目標的主力軍
“可再生能源對我們國家能源供應的作用,簡單點一句話就是‘把能源的飯碗端在自己手里’。”黃其勵說,黨中央國務院提倡積極發(fā)展新能源,我覺得是非常符合能源的特點,也符合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。能源轉型,包括“雙碳”目標的實現(xiàn),主力軍未來就是新能源。
黃其勵表示,可再生能源的首要特點是“本土化”,都在我們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,不需要進口。我們國家可再生能源豐富,太陽能可以裝機456億千瓦,風能87億千瓦。這個資源既立足于本地又非常豐富,因此可以這么說,我們國家能源的稟賦特點是富煤、少油、貧氣、富再生。
黃其勵提出,目前我國能源的主力軍還是煤炭,未來可再生能源會逐漸成為主力。去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56%,清潔能源包括了天然氣、風能、水電、太陽能加在一起比重25.4%。這個比例顯然不是最佳的,但是現(xiàn)實的,未來還要不斷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占比。
不過,目前來講,可再生能源還有兩個缺點,一是對天氣情況的依賴性,發(fā)電有隨機性、不穩(wěn)定性,二是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發(fā)展后,電力系統(tǒng)的“雙高”特點(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和高比例電力電子化),這和電力系統(tǒng)需要穩(wěn)定運行、用戶需要安全供電就產生矛盾。
對此,黃其勵認為,任何新生事物都優(yōu)缺點并存,我們的任務就是不斷的改進,用科技創(chuàng)新來解決這些問題,確保新能源的快速發(fā)展。
顧大釗表示,“雙碳”目標下,國家能源集團未來也一定是“兩條腿走路”,一是提升煤基能源對低碳轉型的支撐作用; 另一方面加快發(fā)展可再生能源。
據了解,國家能源集團一直積極推進氫能發(fā)展。顧大釗認為,未來,氫能可以在儲能方面發(fā)揮更大的作用。電是無法儲存的,我們國家可再生能源發(fā)電還存在棄風、棄光、棄水情況,如果把這些能源轉化為氫儲存起來,可再用于發(fā)電和燃料等。
談煤化工節(jié)能降碳
降低CCS成本將具有顛覆性意義
對于煤化工產業(yè)節(jié)能降碳的路徑,顧大釗認為,煤化工產業(yè)因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較高,除了要通過技術創(chuàng)新來提高煤轉化率,還應關注CCS技術,如果未來一旦成本降低可大規(guī)模推廣,將給減碳帶來顛覆性地改變。
據了解,碳捕集與封存(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)技術是指將CO?從工業(yè)或相關排放源中分離出來,輸送到封存地點,并長期與大氣隔絕的過程。這種技術被認為是未來大規(guī)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、減緩全球變暖最可行的方法。
“我國現(xiàn)在每年大概排放100億噸二氧化碳,據估計,我國可以埋藏二氧化碳的地質容量是2.4萬億噸,但為什么現(xiàn)在埋的很少呢?主要是成本問題。”顧大釗說。
從去年到今年,歐洲碳交易市場十分活躍。歐盟碳價屢屢刷新紀錄,這也間接提升了綠色能源技術的投資價值和經濟效益。更高的碳價意味著企業(yè)排放成本愈發(fā)昂貴,像CCS這種新興清潔能源技術的成本效益大大提升。
“前兩天歐盟碳交易價格已經超過90歐元/噸,就是每排1噸二氧化碳,需要多付90歐元的成本。這就和以前的買賣關系完全不一樣了,以前我把煤賣給你,你要給我錢。現(xiàn)在反過來了,我賣給你二氧化碳,我還要給你錢。假設說你把一噸二氧化碳拿走了,我給你800塊錢,如果說你有技術把他埋起來,假設封存成本500塊錢,你不就賺了300塊錢嗎?”顧大釗說。
據了解,幾年前,國家能源集團成功示范了30萬噸的二氧化碳封存(CCS)項目,掌握了CCS的整個技術流程,核心的技術和裝備,但成本還比較高,主要是規(guī)模相比較還小。顧大釗認為,一個技術從提出來到成熟應用一般需要20年-30年。規(guī)模增加后,再加上技術逐漸成熟,未來CCS的成本一定會下降。所以說CCS應該是一個重大的戰(zhàn)略研究方向。